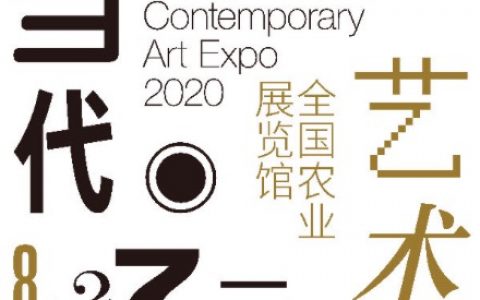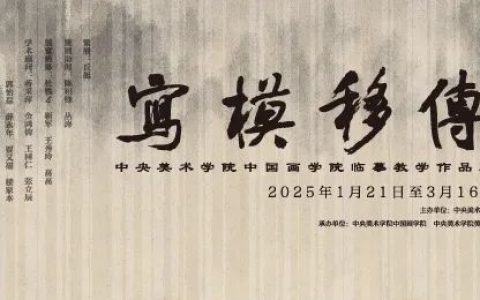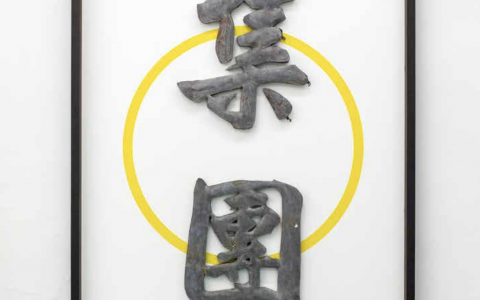Scientific Art and Artistic Science
在19世纪以后,人们才认为科学是一种理性的过程,因此,是可以用数字或公式推理的,而艺术是直觉,是不能描绘的,因此应当置于科学之外。实证主义的科学文化莫名其妙的培育了一种未经证实和不符合客观的信念,即由于人类为了认识世界和自身,将知识分成了科学和艺术,于是人类也就必须分成了科学家、艺术家或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画家、音乐家、文学家等等。这种分类的做法仅是为了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但当这种分类一旦限制了我们更完整地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话,那么分类法的改进和完善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了。这种分类法固然比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要进步,但它客观上还是造成了我们这个世界被机械地分割成几种门类,使我们误解这个整体世界仅是已被证实、命名的数种门类之和所构成。这种思维方法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即将进入21世纪时所应具有的观念和方法。将要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迫使我们反省近十几年来靠“引进”形成的加工工业机制上的问题。我们还看到一种现实:中国的科学家对艺术的理解程度或中国的艺术家对和学的了解,使我们的科学家与艺术家之间好似隔了一座山,相互很少沟通、启发、共事这反映了我们对科学和艺术在认识论、方法论上的落后。
科学与艺术的目的是相同的,方法也是相通的。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本质以及人类存在的背后,究竟还有什么影响自然,影响人类命运,令人惊异的谜在等待我们去揭开这个主题自古以来就是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以至僧侣、道士们为之探究的目标。本世纪的许多发现和发明已开始同人的常识和理智相矛盾了,许多生活中的经验、人的感官感觉在空间的弯曲、时间的脑胀以及形象思维、灵感思维面前无能为力了人们正常的经验和理智使人们局限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三维空间内,而不可能把握四维乃至多维的概念。用现代科学家与现代艺术家作类比,非常合适描写当代科学的世界图景现代艺术和现代科学两者都同时诞生在20世
纪最初的十年期间。同过去的时代相比,这两者都失去了他们表现手段的直观明确性。艺术家和科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不在于他们的目的,而仅仅在于他们彼此所处的角度所用的手段,两者都在寻取对现实的理解就如同人的左、右脑,各主一类功能但其相互配合、协调进行思维一样。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历史期间,人类对自然的解释固然是肤浅的,但却大多从自然的整体去认识。从这一点说,是符合多元文化的自然之本质。因为客观世界中的任何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都是由多种因素交叉:综合所导致的,而不是由割裂开来的某一人为分类所导致。上几个世纪,科学在工业革命中被分离出来--我们现在称之为小科学时代。由于当时科学家能在具有大量空白的基础上,向纵深迅速开拓,使人们陷人了一种由于工业革命以来大分工的惯性漩涡里将本来是由多重原因制约的自然现象,人为地分离成各种孤立的学科以至更细的分类造成了科学家沉湎于由局部认识整体的研究方法,实验科学的相对性将各科学门类机械地割裂开来,使科学家们还不能认识系统理论与方法的威力。
但综合的时代、大科学的时代,随着以电脑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的悄悄来到,边缘交叉学科的大量诞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的出现,以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科学界正面临一场科学方法论的转变,“风马牛效应”“模糊”论不再是不相及和糊涂的意义,在对付瞬息万变的知识价值革命中,重构研究学派,提出新研究方向,建立新术语、新方法形成新知识结构正是当代中国科学界面临的选择。
威廉·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说:“科学是同时涉及事实和推得事实的知识的科学。而不是只涉及事实本身,不涉及推得事实的知识的科学。”
马利坦在《神性》第十章中说:“我们看到的相同的内容的科学进步史--严格地说,可能是从伽利略的物理数学科学以来的
历史--是把感觉现象改为量的符号形式的技艺,这是明显的。”
科学是人类对客观自然规律的不断揭示、发现和描述,是从个别中揭示一般,从个性中抽象出共性,并且是永远无止境的探索、发现、描述,但永远是人对客观的认识进程之描述及认识方法的总和。而苏格拉底在论柏拉图时说:“艺术家恰当地安排万物驱使事物的这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和谐一致直到他创造出一个规则的有序的整体。”
亚里斯多德在《动物分类》一书中写过:“艺术的蕴涵于创作之先构想的形象之中,然后才有形于物。”
马列坦在《艺术与经院哲学》一书的二章中说:“艺术,因为规定了必须是创造,而不是制作,就超越了'自然’范围。”他还在第一章写道:“艺术像科学一样,可以被理解,但要用自己的语言。
艺术是人类对客观自然的主动性认识,是从一般中发现个别,从共性中求异、求创造。是人为的第二自然,是主观的、限定性地从各自的评议、侧面、手法、形式去描绘一个全新的“自然”。也就是说,艺术可以不拘一格,不限其手段、形式、材料在创造比真实自然更完美和谐的第二自然的过程中表现人类的精神世界。
由此可看到,科学与艺术要有区别,只在于科学是求同,艺术是求异(可用不拘一格的形式、各自的语言去创造)科学是发现,艺术是发明,都是过程、结果、方法的总和。都需要严谨、条理、敏感、创造性地、光彩夺目。科学是先假设,再证明和描述第一自然,艺术则也是限定地表现第二自然。只是:科学先前只属于自然科学,艺术则多以为在人为事物范畴。然而当今的时代,这两者所涉及的领域在事实上已相互融合了。
科学学和艺术学都同属哲学范畴的不同侧面,正因为科学与艺术都是抽象的精神,是非物质的,所以研究科学和艺术的学问必然是哲学的任务。
德语称科学为 Wissenschaft,其指的是知识、学问之本意,它不是特指某一科学工作的对象、内容、范畴,而是对人类知识的总称。作为知识的含义,人类首先最关心的是如何抓住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以便驾歌变化着、运动着的世界。这种知识应当被解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方法,而不仅针对自然科学,更不是指具体的材料、工艺、设备、技术那些“硬件”。科学之所以有力量,正是有观念的指导、方法的保证和组织机制的控制,这种成系统化的知识才能被称为科学,
研究这种学问的理论和方法在60年代末开始被人称为科学学,也称为科学哲学。
爱因斯坦在《相对论》附录中论述科学时,反对把科学同分类、编辑等同起来,他主张直觉和演绎思考在科学发明中有同等重要地位还说:这种系统的思想是根据逻辑的方法,由少数称为公理的基本假设而建立的。我们称这种系统的思想为理论。理论是否成立,要看它是否与许多单个观察的现象相符合,这一点就是理论为“真”的所在。
拉瓦锡在《化学原理》序言中坚持科学须由三样东西构成:事实、描述事实的思想和表达这些思想的词汇。但要改进科学时,要同时改进它的语言、术语、思想、结构,否则只能向别人传递假的印象。
由此可以看出,“科学”发展到当代已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学问,它不仅要从整体上、从事实中去分类、分析,“形而上”地描述客观世界;作为“科学”必须在分析、抽象的同时,还要重新整合、重构新的系统,以形成新的语言、新的秩序、新的思想、新的体系。这具有主动的创造性,所以在理性的逻辑思维过程中必须融合大胆的假设和艺术家的直觉,这种思维方法就像一个精巧的筛子,它是有效与骗人、信号与混乱的仲裁者,如何才能在无止尽的数字方程中寻找、沟通正确的联系也一样要靠丰富的想象力。即科学同样需要具备所谓被艺术“专利化”了的直觉、想象力和灵感去编织理论。H.彭加勒写道:“纯逻辑永远也不能使我们得到任何别的东西,它不能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任何科学也不能单独从纯推理中产生。”在科学上每一次巨大的飞跃,往往是科学家对美的想象。这正是由于科学的过程中融进了艺术的方法所致。
重视科学的历史主义、人文主义,即科学的文化背景使科学具有了哲学的时空观,在这个系统的抽象活动过程中,各因素或各子系统之间不再仅是因果关系,也有自由约定俗成的非逻辑关系。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的确具有比任何事物更自由的想象力,它有无限的能力去从事各种方式的分割、混杂、综合,它可以相当松弛地处理经验事实与人类高级思维形态思辩、想象的关系。正是运用了这种科学学的思想,爱因斯坦才有可能发明广义相对论,使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哲学观念的传播发生了重大转折。
德语称艺术是kunst,指人造的、人为的,即艺术。它并不只是指艺术的形式、对象和技巧,也不是指绘画、音乐、文学,而是泛指一切人为的,用一定符号、形式表达人们对自然、对人生的再创造的过程和心智。
艺术的特征必须异常鲜明、形式感很强,有一定刺激性、挑战性、比喻性,从个别、局部直观地“形而下”地创造一个人为世界。正因为艺术再创造的是…-个第二自然,一个具有新结构、新秩序、新符号的系统,所以从表面上似乎是偶然的、经验的、主观的形式,而背后有一个无形的网络存在。艺术并非是形象、色彩、符号、材料、技艺的堆砌,而像一只似乎简单的鸡蛋,虽然是个“单细胞”,却隐藏着无限的生命力。它是个有机的整体,是个有血有肉、有骨头的体系。艺术与技艺的区别就在于此,它不是模仿、制作与再现,而是被规定要有思想,要用独特的符号、自己的结构、新颖的形式,以耐人寻味的情调、风格去表达特定的思想。它源于真实,却高于真实。
中国艺术讲究的是神、势、气。中国历来主张“师法造化”“观象于天,观法于地”“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古代中国先哲的时空观是互补共生的,并不像西方近代哲学和科学将时间与空间隔裂开。这种古代中国的艺术哲学是一种朴素的整体美学观,是强调精神、强调人的主动性、强调创造性的。使艺术创造拘泥于象形、图解,追求“术而不作,慎终追远”的“八股”套路;将艺术这种“形式的抽象”歪曲为“抽象的形态”,将传统的精神理解为符号的继承、形式的因袭,忘记了艺术的真谛是创造新符号、新秩序、新形式、新思想的过程:“传统”不应是以实体为形式,不应是外在的显露的符号重复,而应是内在的、潜意识的,人文化了的“事”中之“物”所体现出的人类智力、精神风格、韵律之凝聚,并且是在不断发展、演化的积淀过程;对艺术的这种理解必须摆脱仅靠经验、直觉、感觉的束缚,要把智力、知识、经验从身体的有机部分分离抽象出来,以形成科学的理论、抽象的思维,方能摆脱具体形式的限制,形成创造性的精神成果。比如肉和肉汤是靠感官的感受,靠经验和直觉形成一种认识,它不具备抽象的联想,算不上是创造,也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一日理解建筑的柱子、工作灯的支架、眼镜的腿汽车的轮子、卧铺车厢的折叠凳子所附着的车厢壁等都与人的两条腿具有同等意义,这种运用抽象思维的方法,认识事物本质属性,并运用联想去创造性地掌握造型艺术规律的过程才是艺术科学的要领。司马光之所以能“破缸救人”,就因为他具备了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大胆的创造力,也就是把真实生活中熟视无睹的信息、符号、现象重构于一个新形式之中,也必然表达出不同凡响的
思想,这样的艺术再创造已具备了科学的翅膀,也就不会沦人“匠人”的造作之流。
艺术虽是凭感觉的,但人的感觉并不孤立存在于真实之中。人的感官已经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从生理器官向文化器官演进了,所以人的感觉是完全可以抽象为感知,直至对形式美法则的认识。忘记符号、结构、法则的起因,滥用媒介形式,就会陷人形式主义之中,反之,随着对第一自然的本质分析,找出其规律法则和起因,便能从“造型”的活动中摸到被创造的第二自然美。所以人吃了牛肉不会变牛,而能壮筋骨、旺精神就是在客观事物中分析了其基本要素--葡萄糖、蛋白质、维生素等等--即本质。这个过程在生理上称之为“消化”,在思维上称之为理解。科学和艺术的相乘就像人们用左右脑一起思维的过程,艺术要能创造,科学要能飞起来,只有将科学学与艺术学这两门哲学的分支融合起来,那么科学与艺术会在中国重放光彩。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大科学时代的数学、物理的高度抽象、非欧几何、拓扑学的时空统一都使艺术处于一个重新构建语言、符号、范式的时代,艺术之抽象将与艺术的直一觉并驾齐驱,艺术的大众性将被艺术的参气性所丰富。即使没有“艺术细胞”的人们也完全可在键盘的跳跃中领略到艺术生命的搏动。三维空间性的图形在“时间维”中的概念重组和动态艺术的跳动使人们更易认识到艺术必须与科学同流,是再创造的过程,并很容易理解的艺术的形式、艺术的评论、艺术的体裁与艺术的思想是一种不可分的创造过程,也是一门科学。这正体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共同任
务--对人类思维和想象力的开发。在这个客观对象已被认识是系统化了的,研究方法也已系统化了的,连手段、技术也系统化了的时代,思维方法不系统化是不可想象的。科学与艺术的互补、共生将使科学、艺术本身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就是科学学与艺术学的本质将在思维活动的破译中被科学家、艺术家所接受。科学家也许不再一定用数字、公式来描写自然,也许是形象的、模糊的图形;艺术家也不只偏爱色彩、形态这些纯物质的语言,而会探索由各种信息、各种方式,甚至是抽象的、软的组织去创造更有想象力的、更健康、更合理、更美的生存方式、生存空间。
(柳冠中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